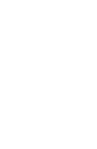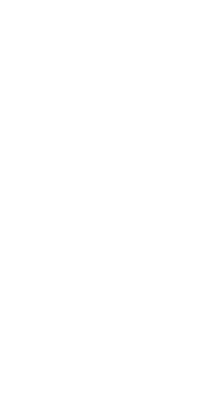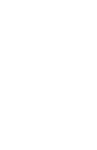字号
A-
19
A+
默认
背景
1.5 南柯一梦
郭笨聪虽然身体强壮,但在海水里泡了小半天,再加上一整天的折腾,又困又累之下,竟然趴在桌了睡着了。
过了许久,郭笨聪终于醒来,却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;旁边坐着自己的父母、同学、大学的班主任,甚至他暗恋的那个女孩子也来了。这些人均是面带微笑,目不转睛地地看着自己。
郭笨聪忽地从病床上坐起,心中大喜过望,原来那些浮尸、火矢、陆秀夫、皇帝,竟然是一场恶梦,如今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;只是,那个梦却是如此真实,以至于他觉得现在的情景才是做梦。
他想了又想,直到想得头痛,可就是什么也想不起来,急问道:"我是昏迷了么?我睡了多长时间了?"却没有人回答。他又提高声音更大声地问道:"你们告诉我,我昏迷了多长时间了?这里是医院吗?"
旁边的父母,同学,老师,朋友只是微笑地看着他,并不回答。郭笨聪大急,高声道:"你们回答我呀?"这些人仿佛没有听到一样,任凭他如何叫喊,就是不做声。
忽然,病房的门"吱呀"的一声开了,外面阳光刺目。郭笨聪看不清是何人走进,辨其身影,像是个女护士。
待这护士走近之后,郭笨聪吃惊不小。这护士模样,他似乎认识,可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,忙问道:"我在哪里见过你吧?"这护士也不答话,从怀里掏出一件物品放在桌上,转身便走。
郭笨聪心中大急,想要高声喊叫,却发现无论用多大力气,就是喊不出声,再转头一看,却见这护士放在桌上的东西,竟然是一条发束。
郭笨聪顿时想起了这护士的名字,当下大声叫道:"听琴!听琴!你别走,我还不会戴发束!"如此喊了几句,猛地惊醒过来,却是南柯一梦。
窗外传来的,是海浪拍打船舷声;面前摆着的,仍是那张旧书桌。郭笨聪的心一下沉到了底。
"公子…公子是否有事?"门外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,正是听琴。
郭笨聪吃了一惊,未想听琴竟然就在附近,忙打开屋门,却见听琴果然就站在门外。他顿时惊呆了。
听琴看他睡眼惺忪的样子,衣袖上湿了一大摊,嘴角仍然挂着口水,又拉成丝状连到前襟之上,瞪大了双眼说不出话,过了半晌,这才结巴道:"公子…可是要我帮你戴上发束?"
郭笨聪愣了一下,应道:"是啊,还请姑娘帮我。"
听琴点了点头,脸上惊诧之色未去,又将郭笨聪上下打量一番,说道:"公子还是先洗脸吧。"说着,取过墙角的木盆离开,片刻之后又返回,手中端了半盆热水,将盆置于地上。
郭笨聪胡乱洗了一番,后又回到桌前,笔直地坐在凳上,摆好姿势,问道:"听琴姑娘,为何你正好在门外呢?"
听琴边替他梳头边答道:"我在门外叫公子的名字,却无人应答,心想公子定是累极,故而睡得极沉。我正要离开,未想又听到公子唤我。"郭笨聪奇道:"姑娘一大早找我,可是有事?"听琴道:"也不算是一大清早,如今已是巳时了。"
郭笨聪茫然道:"竟然已到巳时了。"口中如此说着,心里却是一团混乱,他根本不知道巳时是几点钟,忽又想起子时就是半夜十二点,忙在心中暗自背诵起来"子鼠、丑牛、寅虎…",扳到第五个手指的时候,终于数到了"巳蛇"。看来,"巳时"应是上午十点左右。
听琴看不到郭笨聪的表情,只见他的手指逐个合向手掌,像是在数数一般,颇为惊诧,心想:"郭公子既识天象,必定也懂得周易理学。他此时扳着手机,想是在掐算甚么重要的事情吧。"刚想到此处,忽然看到桌上那三本书,随意瞅了一眼,好奇之心顿起,问:"公子的书本好生奇怪,上面的字如此小,又画些奇怪的符号,可是用于占卜的易学书籍?"
郭笨聪呆了一呆,随口答道:"姑娘猜得没错。倘若学会了书中的知识,不仅可以占卜预测,还能造出打败元军的武器。"如此说着,又想起了自己立下的宏图大志。
听琴惊道:"打败元军!公子所说当真?"
郭笨聪暗骂自己嘴快,竟然将这事随意讲出,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明确的想法,忙又连连摇头,叹道:"咱们现在只有十几条船,要打败元军自是不易,况且制造兵器也不简单。"
听琴急道:"公子别动!你这一摇头,我就没法为你束发了。"
郭笨聪一动不动,又继续问道:"听琴姑娘,你在门外叫我,可是丞相找我有事?"听琴道:"这倒不是。后舱搭起了灵棚。公子何时去守灵?"
守灵?郭笨聪长这么大,还从未给谁守过灵。他依稀记得,古人守灵好象要七天七夜,也不知是真是假,又或是各个朝代的规矩不同?那宋朝是守几天呢?郭笨聪完全不知,又觉得此事万不能推脱,遂答道:"自然要尽快去了。"
话音刚落,听琴已梳好了头,接口道:"既是如此,公子用餐之后,便去灵棚吧。"郭笨聪忙道:"好,先吃饭,后守灵。"
听琴看他一脸糊涂状,料其不知在何处用餐,又道:"公子跟我走吧,我带公子去餐房。"郭笨聪连连点头,手忙脚乱地将桌上的书本收拾起来,放入床下的小柜,跟着听琴走出房门。
所谓餐房,其实是船上的一个大舱厅,然而设施却是一应俱全,毕竟这是皇帝乘坐的龙舟。能上这大船的,均是朝中的要员。此时的宋朝庭,所有的重要官员,连同后宫成员,几乎全在这大艘船上。
郭笨聪匆匆用完餐,走上甲板,行至后舱,放眼望去,吃惊不上。整个后舱放满了棺材,其中有些棺材极为考究,显然不是临时制作的。
地上跪了几十号人,均哭喊着不同的名字,想是这些逝者的家属正在祭拜。
在南宋末期,江以已被蒙军完全占领,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也陆续失陷。陆秀夫等人知道元兵迟早会攻来,一场恶战在所难免,早就为朝中大臣备了棺材,人称"携棺而战"。此句成语在当时极为流行。
宋朝百姓但凡加入军队的,家中都会为其备一副棺材,并且剪下一缕头发放入棺中。如此一来,即使将来战死了,不管尸首是否能够寻到,家人也可将棺材埋了,这总比那些"衣冠冢"要好一些。
然而元军步步紧逼,在那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崖山海战之后,宋朝将士全军覆没,十万百姓跟着投海自尽,"携棺而战"这句成语,竟然从此失传了。后世的学者们只在典籍中找到"携棺"二字,却无从考证其起源。郭笨聪机缘巧合地回到宋朝,竟然成了唯一听过此句成语的后世人。
且说郭笨聪,进入灵棚之后,正四下寻找郭长发的灵牌,忽听旁边有人说道:"贤侄来了?郭尚书的灵位在这边。"听其声音,正是陆秀夫。
郭笨聪忙应了一声,紧跟着陆秀夫,穿过十几个灵位之后,到了灵棚的最**。此处立了三块灵牌。郭笨聪仔细看去,顿时吓了一跳。这三人的官职竟然极高,分别是"兵部尚书郭长发"、"礼部尚书吴连城"、"户部尚书铁树封"。
除了郭长发,郭笨聪从未听过其余二人的名字,也未曾在历史书箱中看到过,心中颇为不解,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,为何书本上从未提起呢?
其实在南宋的最后两年间,朝庭重要职位的变动极为频繁,有时候第一天刚上任,第二天就殉职了;有的是上任没几天,发现元军攻势猛烈难以推挡,便当了逃兵;更重要的原因是,大家均知宋庭已是强弩之末,因此无论多高的职位,大家都不愿意上任,职位越高死得越快。正因如此,历史书中记载的名字,都是南宋灭亡前几年的人物。
陆秀夫道:"贤侄,郭尚书的灵牌虽然立了,但立牌人的名字还没有写上。"
郭笨聪又看过去,只见这三个牌位的材质完全一样,白底黑字,像是出自同一人之手,想是朝庭在出海之前,早已为每人做了灵牌。其它两个牌位上,一个写了 "不肖子吴卫夫",另一个写了"孝子铁木三",当是两位尚书的儿孙们写的。再看郭长发的灵牌,其下方却是只有一个"立"字。郭笨聪知道自己也要在上面写上"孝孙郭笨聪"---不,应该是"孝孙郭本存"五字,又或是"不肖孙郭本存"这六字。
旁边有太监递过一支毛笔。郭笨聪伸手接过,额头已开始冒汗。他只在幼时学过一年毛笔字,而且只有三字写得最好,那便是他的名字。如今,他要写的并非自己的名字,而是"郭本存"三字。
郭笨聪知道这一关非过不可,索性豁了出去,道:"丞相,其实在两年前,晚辈已改了名字,虽然发音还是一样,字却是不同了。"陆秀夫听得惊讶,口中却道:"既然如此,贤侄只管写上新名字便可。"
其实陆秀夫根本无瑕思考郭笨聪的言语,他可不像郭笨聪这般只想着自己的安危。大宋朝庭虽然侥幸脱险,但他的妻儿却也丧命,然他只能悲痛片刻,马上又要面对更重要的事情:清点船只人员,摸清船队所处的位置,分析元兵可能的追击路线,沿途是否有岛屿,岛上的人与大宋关系如何,船上的粮食是否足够,武器装备情况……所有的这一切,他必须在一天之内调查清楚,还要对下一步进行决定。这已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了。
今日上午,陆秀夫原本不想出现在灵堂,然而昨日的死者中,有不少是朝中重臣,按说皇帝应该亲自前来,只是赵昺昨日受了惊吓,无论如何也不肯走出船舱,陆秀夫只好自己亲来。
且说郭笨聪,听说允许写自己的名字,心中总算有了底,伸手接过蘸满了墨的毛笔,又偷偷观察了另外两块灵牌,心想五个字总比六个字容易写些,当下写了第一个字"孝"。再要继续写"孙"字,却发现另外两个牌位上并无此字,心中犹豫一阵,也不知道"孙"的繁体字如何写,忽然又想起"子系中山狼"这句词,心中顿时醒悟,原来这"孙"的繁体写法,是左边一个"子",右边一个"系"。
写完这两个字,郭笨聪心中大定,因为接下来要写的,是他早已练习过几千遍的名字,狂喜之下,不及思索这三字的繁简写法是否相同,却想起以前听过的一个故事,正好应了眼前此景:
有个当官的人叫胡不字。这人没有文化,又不愿意学习,然而他又要在审批材料上签字,因此只学了五个字"同意。胡不字"。日积月累,胡不字每天都要写这五个字,竟然将这五个字练得极为纯熟。有一次,胡不字去日本考察,日本官员让他签一份文件,胡不字写下了自己的名字,这官员顿时惊呼道:"胡先生这字写得好啊,笔端夭矫,意在笔先,力透纸背。"一时,胡不字在日本官员之间成为神谈,众人执意要胡不字题词。这下可急坏了胡不字,他只会写五个字,如何给人题词?这不要闹国际笑话么?胡不字机灵一动,立时有了主意,挥笔写了一首诗,诗曰:同意不同字,同字不同意;意同字不同,字同意不同。这首诗只用了五个字,又正好是他会写的五个字,却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中国汉字与日本汉字的区别与联系。
郭笨聪一边写着自己的名字,一边暗自寻思:"我在木牌上写字,自然无法"力透纸背",不过要"入木三分",却是毫不夸张。"忽又想起了"胡不字"的典故,嘴角已露出笑意。
写完这五个字,郭笨聪长舒一口气,正要放下手中的毛笔,忽觉周围气氛不对,忙收起笑容,再一抬头,却见众人都在齐齐看着他,脸上均现出极为怪异的神色,像是见到了不可思议之事。
这也难怪。陆秀夫让郭笨聪写上自己的名字,在场的十几人听到声音,均将目光移过来看着他。
众人看他先是眉头紧皱,继而又眼中放光,待写上自己的名字之后,忽又眼角带笑,几乎就要笑出声来,这与目前的形势极为不合。试问这世上哪有这种人:自己的爷爷在前一天刚刚死去,做孙子的在第二天写灵牌时,竟然还能笑出来?
郭笨聪心中大急,瞬间转过了无数个念头,只想将这局面给扳回来,却又清楚地知道为时太晚,心急之下,忽然灵机一动,脱口道:"丞相,晚辈想到了击退元军的办法!"话刚出口,已不似前阵那般慌乱,却又多少有些后悔。
以郭笨聪的理解,人在正常情况下是面无表情的。如果有高兴的事,就会笑;如果有悲伤的事,就会愁;如果又有悲伤的事,又有高兴的事,那要看哪个程度大了;倘若值得高兴的是一件大事,但令人悲伤的是件小事,那总体上还是高兴的,因此笑出来也不为怪。如今,祖父虽然去世,但朝庭却有了救,又或是可能有救,总体上还是值得高兴的,笑出来也算正常。
刚才那话说出之后,郭笨聪又是安心,又是后悔。安心的是,这正好解释了他为何突然发笑;后悔的是,如此胡言乱语,也不知接下来该如何收场。
陆秀夫吃了一惊。旁边众人亦是同样心思,面面相觑。有几人已暗自摇头,心想这少年定是因为祖父离世过于悲伤,以致心智渐失,开始疯言疯语起来。
陆秀夫急道:"贤侄此话当真?"郭笨聪道:"晚辈不敢胡乱说话;即使没有十足把握,但多少会起些作用。"他说此话时,言语间又开始含糊起来,心想话不能说得太满,免得到时无法收场。
陆秀夫与周围几人交换了眼色,道:"贤侄请去议事厅说话。"说着,与周围几人一同离开,又示意郭笨聪也跟过去。
郭笨聪忙紧随众人,一路行去,进入主船舱之后,下了楼梯,最终走入了一间房子,正是大宋朝的枢密院。